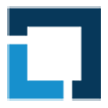辛迪的身子晃了晃,倒了下去。霍德华得意地吹了一下冒着硝烟的枪口,弯腰将枪在辛迪的右手手指上按了按,以便留下辛迪的指纹,然后在离辛迪右手不远处将枪放下,一个持枪自杀而死的人,枪是不可能还握在手上的。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霍德华背上一个大包,迅速带上门逃离现场,登上了那辆小面包车,不过,他没有开车灯,以免有人发现。远远地,他从车窗后面看见有几个人影正向他的小屋奔去。显然,枪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他一路吹着口哨,笑了。明天一早,警方就将会将霍德华畏罪自杀的消息公布于众:一个罪大恶极、走投无路的杀人犯在自己的藏身之处选择自杀,这很合乎情理,房间抽屉里有霍德华的证件,“霍德华”身上又有一封写给父母的遗书,这些足以证明霍德华已经离开了人世,通缉令也就成为一张废纸了。
1939年秋天,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某部队行军路过我的老家,在那里进行了短暂的休整,官兵们分散到老乡家里住宿。村里有个叫杨立秋的富裕户,家里住进了一湖南老兵。
这杨立秋家的房子分前后院,后院和前院连在一起,同走一个大门口。杨立秋和老伴住前院,儿子杨金友单身未婚独住后院,到后院去须从前院房子穿堂而过。
湖南兵被安排在后院与杨立秋的儿子杨金友住在一起。湖南兵住下后,好像对杨立秋家的房子很感兴趣,一有空就屋里屋外看个不停,有时跑到院子外边围着房子转悠。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趁杨金友睡着了,他顺着梯子爬到房顶上,一趴就是大半夜。有好几次见到杨立秋他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表情很是怪异。问他,他又支支吾吾地说没有什么事。直到部队临走的前夜,湖南兵才郑重其事地对杨立秋说,“大爷,你们这房子出过什么事没有?”
杨立秋联想起几天来湖南兵的种种神秘行为,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反问道:“怎么?莫非你看到了什么不成?”
湖南兵吞吞吐吐地说:“没……什么,既然没发生过什么就算了。”
杨立秋说:“老总,如果你看到了什么,请千万告诉我一声,我们一家人忘不了您!”
湖南兵这才说道:“不瞒大爷您说,我那天一进你家门就感到阴气很重,晚上在房顶上我看到房子后面的石碾上有个东西,有时就跳进你家后院里。根据我的经验,我敢断定你家三年内将会出现癫汉(癫魔病人),而且专门癫刚进门的新媳妇。”
杨立秋一听,不禁大惊失色,一下瘫坐在地上。原来一年前的一个晚上,村里有个姑娘私自与邻村青年幽会,怕被夜归的杨立秋撞见。多事的杨立秋把此事告诉了姑娘的父母,结果姑娘遭到了父母的暴打严责。姑娘是个烈性女子,一时想不开,便来到杨金友房后的石碾上上吊自尽了。此后,村里再也没有人用过这个碾。杨立秋觉得姑娘的死与自己有些干系,因此心里总是郁闷不安,想不到早晚还是要出事,这可如何是好?他急忙问道:“请问老总有没有破解的方法?”
湖南兵道:“有是有,只是我们部队有纪律,我不敢帮你破解,只能告诉你这些了。”
第二天,湖南兵就离开杨家随部队出发了。
自此之后,杨立秋整日忧心忡忡,先后请过几个巫师和阴阳先生。但看过之后都说没有什么大事,是湖南兵故意编出来吓唬他的,只要逢年过节到碾上多烧点纸钱就可平安无事。杨立秋听了之后略感欣慰,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就把这件事忘了。
一年之后,杨金友年满二十,经人介绍,与邻村一姓陈的女子喜结良缘,新房就安排在杨金友住的后院房里。新娘子进门后,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一家人和和睦睦,全村人没有不夸的。
新婚蜜月刚过,这天晚上,杨金友到朋友家喝酒,酒后几个年轻人又玩了一会儿牌,不觉已是深夜。因时间太晚,杨金友怕从前门回家影响父母休息,又怕父母责骂,就想从房后让妻子打开后窗跳进新房。这样想着,就抄另一条路向房后走去。
这时已是深夜,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自己的脚步声和偶尔传来一二声狗叫,杨金友快步走着,不一会儿就看到自家的房子了。
新房后面是一条死胡同,石碾就在死胡同里,离后窗只有几步远。自湖南兵走了之后,杨金友就对房后的石碾产生了一种恐惧感,此时夜深人静,更增加了恐怖气氛。离家越近,杨金友越感到紧张,心怦怦直跳,呼吸也越来越急促。
近了,离新房越来越近了。透过后窗缝已依稀看到新房里的灯光了。杨金友知道妻子还没有睡,还在灯下等他,心里禁不住涌上一丝温暖,恐惧感也随之消失了。
拐过前边那堵矮墙,就到新房后窗了,杨金友心里一阵轻松,快步走向后窗,举起右手正要敲窗,同时,下意识地扭过头来向石碾上扫了一眼……
蓦地,像电影中的定格镜头一样,杨金友举在半空的手停住了,身体僵立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因为他清晰地看到,在朦胧的月光下,一个衣着鲜艳的年轻女子正坐在碾台上冲他微笑……
月光很亮,杨金友甚至能看清她那张像抹着白粉一样惨白的脸和微笑时露出的雪白的牙齿。
一股冰凉的寒意从头顶迅速传到脚底,杨金友只感到头皮发紧,头发“嘎吧嘎吧”地竖了起来,脸上的冷汗不知不觉流了下来,狂跳的心脏仿佛一张嘴就能跳出来一样,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浑身绷紧得像石头一样。
来不及多想,杨金友一边失声叫着妻子的名字,高喊“快开门!”,一边握紧拳头,用尽平生的力气奋力向后窗砸去……
“哗啦啦!”随着一声巨响,后窗上手腕粗的窗框一下断为两截,窗门大开。
随后,杨金友像疯了似的一头钻了进来。
屋里,新娘子正坐在炕沿上做针线活。突如其来的响声吓得她魂飞魄散,抬头见丈夫头发直竖,脸色惨白,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新娘子更加恐惧,竟一下仰倒在炕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惊魂未定的杨金友眼见妻子昏倒在炕上,赶忙扑上前去摇着妻子哭喊着“娘子,你快醒醒!”
片刻,新娘子悠悠醒来,睁开眼看看杨金友,再看看周围的一切,突然惊恐地喊道:“你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说罢,坐起来又哭又笑、又喊又叫。
新娘子疯了!
此后,虽经多方求仙拜佛、寻医问药,新娘子的疯癫症却一直未见好转。杨金友经此惊吓和打击,也变得忧郁寡欢,不思进取。面对这一切,杨立秋经常唉声叹气,间或狠擂自己的头。杨家从此一蹶不振,家境日渐衰落。
2001年春节我回老家过年,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喝酒聊天。二大伯讲此故事,吾记之。
阴历七月,天热得似乎把地皮都烤出烟来,就在这样的天气里,却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在急匆匆地赶路。突然间,年轻人停下脚步,蹲下身体拨开路旁的草丛,露出一块被杂草遮掩住的界碑。界碑看样子有年头了,上面的字迹都有些模糊不清,但还能勉强辨别出“谢家村”这三个字。
年轻人轻舒了一口气,风餐露宿地奔波数千里,今天终于赶到了。路旁有一户人家,年轻人上前轻轻地敲门。
门开了,一个老汉探出头来。年轻人微笑着问道:“老人家你好,请问这里是否有个叫谢芙蓉的人?她现在住在哪里?”
听到这个名字,老汉皱眉想了一会儿,猛然间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哦,你是说惠贤师太呀,她几年前就出家了,就在北面十里外的清云庵里。”
看到年轻人露出惊疑的神色,老汉叹了一口气说:“听说当年谢姑娘的心上人出去闯荡江湖,至今未回。后来谢姑娘的父母几次三番地逼她嫁人,谢姑娘受不了逼迫,一气之下就出家了。”年轻人点点头,向老汉拱手道别。
清云庵建在小山顶上,由于平时香火不盛,所以显得有些陈旧。年轻人敲开大门,对庵里的人说要找惠贤师太。没过多久,一个神色冷漠的尼姑走到年轻人面前,打量了他两眼,然后说道:“这位施主,你找贫尼何事?”
年轻人赶紧躬身施礼说:“我叫耿长明,是雷克强雷副帮主的徒弟,今天奉师父之命来送一份礼物。”惠贤师太的眉毛一挑,沉声说道:“我的尘缘已了,与雷克强再无瓜葛。他的礼物恕我不能接受,施主请回吧。”
说完,惠贤师太转身就要往回走,耿长明吃了一惊,他赶紧又说:“师父不仅送了礼物,还有几句十分重要的话要我转告师太。”
惠贤师太对耿长明点了点头:“什么话,你说吧。”耿长明没说话,只是四下里看了看,惠贤师太想了想,然后示意耿长明跟她进去。
来到一间很雅致的小屋里,惠贤师太亲手为耿长明沏了一杯茶,耿长明也有些渴了,他拿起茶杯,一口气就喝光了。耿长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正要说话,忽然一瞪眼睛站了起来,指着惠贤师太大声说:“你不是谢芙蓉!说,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冒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