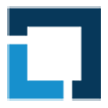观花婆听后,打了一碗水放在桌子上,然后把一张黄色的符咒点燃,只听黄色符纸燃烧后发出吱吱的声音,观花婆在把燃烧的符纸按在水碗里,在用食指和中指搅动了一番,双眼往水碗中看了看,而这过程,两夫妻完全不明所以,不知观花婆在看什么。
半响后,观花婆抬起了头,脸色铁青,道:“你家老母亲被邪灵入体了,说吧,你们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还是做了什么?”
“没有啊,我们夫妻都是老实人,没有得罪人。”
“不可能,要知道凡是都有因果,如果不是你们,那么问题就在你们老母亲手上。”
观花婆说完后,在看了夫妻二人一眼,问道:“把你们老母亲的生辰八字告诉于我。”
两人把老母亲的生辰八字告诉了观花婆后,观花婆开始在祖师爷面前插了一炷香,又化了一道水碗,看明水碗中的事实后,这才说道:“还好你家老母亲惹上的邪灵道行不深,刚刚还处于萌芽阶段,现在我还尚有办法对付,若是你们晚来三天,那就完了。”
原来前些日子,老母亲不知从何处捡来一尊邋遢的菩萨神像,因为老母亲本就信服,把菩萨神像捡回来后,用清水清洗,在自行用柚子叶开光,供奉在屋子里,哪知就出事了。
老母亲擅自用柚子叶开光,反而引来了邪灵。
而邪灵的产生多半是怨念的过多,以及长期生活在瘴气的地方,而且邪灵的灵魂将不会获得自由,阳光成为了它的天敌,黑暗永远地降临在它身上,它永远都要痛苦不能解脱,除非有人帮助他升天。
观花婆知道事情的因果后,把办法告诉给媳妇让媳妇回去办就是,媳妇听后,畏畏缩缩的点了点头,夫妻二人离开了。
三日后,午饭后,老母亲忽然狂暴的从屋子里冲了出来,只见她一身邪气,眼睛瞪的比鸡蛋还大,吓得夫妻二人贴在墙壁上,脸色惨白的喃喃道:“我靠,怨气够重的啊……”
“嗷嗷……你们在我鸡血里下了药!”
老母亲脑袋嘎巴转动,脸色没有丝毫血色,浑身弥漫着一股死气,恶狠狠的一步步朝着夫妻二人慢慢走来。
“啊……你不是下药了……她怎么还能动……”
丈夫说话舌头都打结了,惦起脚尖,后背贴在冰冷的墙上。
妻子早吓得说不了话了,点了点头,过了好一会,这才结巴道:“按照……观花……婆的吩咐……下药了……啊……”
然而,就在老母亲一步步靠近夫妻二人时,一道厉光忽然闪耀,一声凄厉的声音响起,妻子这才喜出望外的喊道:“我想起了,这是观花婆那天给我的云海石手链,只要我们有这个,她是不敢靠近我们的。”
老母亲被云海石手链打伤后,在加上之前被下了药,整个人如同小鸡似得,在地上不断打哆嗦,然后口吐白沫,两眼一翻,整个人晕了过去。
事后,老母亲恢复了过来,邪灵也从老母亲身上走了,观花婆告诉夫妻二人,原来这邪灵也是横死之人,那天被下药后,从老母亲身上离开了,本还想回到老母亲身上去,无奈老母亲身体太虚荣,回去也没效了,所以邪灵就想要寻找其他替身,还好观花婆那日早在路口等着受伤的邪灵,直接把它给收了,事情这才告以段落。
“呜……呀”寝室里突然传出一声怪音。
不用怀疑,肯定是对铺的何月又在听鬼故事,正在惊心动魄阶段。
因为上火难得有些失眠的贾女眨吧眨吧眼睛,接着又习惯性的叹了口气,瞪着窗户外面的电信大楼。
“桀桀——”下铺牙齿对碰的声音。
也不用紧张,这是陈晨看小白文看到兴头上发出来的笑声。
天冷……抖的,有点走音。
夜色正好,梦话全无。
清晨起来,贾女稍稍按摩了一下酸软的胳膊,没精打采的从被窝里面爬出来,照传统习俗照了一下下铺友人的镜子。
果然,面色萎黄,眼圈泛黑。凑近一看,眼角还有不少血丝。很委琐啊……看来很有必要调养下。
贾女转身向自己的书桌方向走去。
猛然!一只白玉一般的手挡住了去路。纤匀有肉却指节分明,有青色的经络顺着润白的皮肤蠕行而上,在近手腕处愈发分明。
“贾大,有创口贴不?”是何月,脸色有点白,估摸着可能昨天鬼故事看过了。
“我手指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划了个小口子,昨晚疼了一夜,郁闷死我了。”
贾女抬起那只受伤的左手细看:小指指尖上有一道看似细微实则很深的血痕,如玫瑰初绽。
“哦,还有的,我拿给你”贾女绕过她,从笔筒里掏出两片创可贴。没办法,这片儿的医药卫生基本都归她负责。
“来,我帮你”撕开一个,贾女小心的把它圈在了何月的左手小指上。
“谢谢啊”何月满意的笑了,她用右手蹭蹭贾女的脸,似怜惜似感叹道“我看你气色不太好,我那还有一点玫瑰,你泡点玫瑰红茶喝把,很养颜的哦。”
“不过,”临走,她又故意回头露出诡秘的一笑:“我昨天听了个关于茶的……”
“免了,我马上去自习,时间比较赶,还是改天告诉吧,谢了”
贾女赶紧做时间紧迫状。
何月颇有些失落的走了。
贾女长舒一口气,接着不紧不慢的开始洗漱……
此时寝室里的其他人都已经走了。
有点空。
约过了半小时左右,最后一个人——贾女才踏上奋发之路,目的地——第五教学楼。
那是一栋掩映在重重绿色之中的三层老楼,年代久远,鲜为人知。突出的特色是冬冷夏热蚊虫不绝,好处是人烟稀少尤以三楼为最,向来为各式独来独往人士所钟爱。冰家必到之所,运气好的时候可以达到平均每层一人的奇佳效果。
深得贾心。
贾女习惯性摸到三楼,打开电灯,坐在地三排左第二个位子上。打开一张报纸铺在桌子上,从包里掏出水杯,打开盖子凉着——那是一杯热乎乎的玫瑰红茶,色有点深,是半透明的的酒红,那是贾女在里面加了点醋的缘故,看进去好象在水中间偏上的位置上浮着几朵打苞的胭脂色玫瑰,带有点焦灼的味道。
不管怎么样,贾女总算开始了一天的自习工作……
第一步:看会报纸先……
水杯上的热气尚且很足、很大……
屋子外围的玻璃窗有点旧了,周围乌黑的一圈已经不大能擦的干净……
时间点点点……屋外另人有些意外的出现了一个影子。这个影子并没有一闪而过,他在屋外左右踌躇了片刻后终于迈进了教室,很有幸的成为这里的第二个成员。虽然也许是临时的。
“贾女……”显然的底气不足。
贾女勉强把注意力从报纸堆里拽出来,眯眼一看,原来是本班有名的温吞男侯峻,定义:某只说话完全没有重点的哺乳类动物(爱心泛滥、呵护幼崽),偶尔喜欢坐在自己对面自说自划。出神后不甚娇羞的一低头是其标志性动作,频率基本保持在十分钟一次。
“有事?”脑袋十分的混沌,语气十分的恶劣。
“呃,是这样的,我听说……”以下省略上万字。
低下头,某女继续看报……红茶依然很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