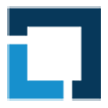第二天,卫知道好不容易攒了二十枚铜钱,在镇上的药铺买了一剂治疗摔伤的药方,带回家中煎煮,服侍云帐服用。云帐略懂一些医术,把脚固定得很好,并没有错位。两人在国都落脚在深林之中,幸亏有云帐及时救治,才将这断脚救回来。伤筋动骨一百天,云帐也不敢大意,在桃花客栈休养了两个月,虽然脚仍未痊愈,但已能活动,拄着拐杖四处走动。云帐心急,卫知道也觉得差不多了,便雇了辆驴车前往国都。
临淮出发的第二天,都城迎来了最尊贵的客人——大国师。武帝特意派四品武官和礼部侍郎带着一队人马在城外十里迎接。清晨微醺,六月的晨光带着一丝凉意,绿秧站在树荫下,看着眼前一条土路横亘在五颜六色的杂尘前。这是进城的唯一通道。迎接贵宾似乎显得有些吝啬。毕竟,这个国家还未足够富强,还不能将青砖铺设到城外十里。
一匹匹骏马不耐烦地低头啃食路边的青草,马蹄偶尔踩踏几下,扬起些许尘土。等到阳光高照,树叶都无精打采地垂下头来,露珠在草丛中滴落到绿秧等人额头上,如珠子般滚落。大国师一行人缓缓而来。
一群僧侣押解着满天尘土,抬着轿子向武帝使臣走去。前面锣鼓喧天,花枝招展,中间抬着轿子飞快前行,后面跟着数百名手持刀剑、背负弓箭的侍卫,气势磅礴,声势浩大。绿秧下马抱拳道:“国师一路辛苦。末将绿秧奉命前来迎接国师。”身后众人纷纷跪下行礼。队伍中走出一个清秀的童子,手持拂尘,高声道:“将军免礼,请将军引路。”说完退回国师身边。绿秧也不多言,翻身上马,带领众人缓缓前进。
一群人从中午走到傍晚,才进入国都。城内道路早已清理干净,不见人马,家家户户闭门谢客。忽然,一个顽皮的小孩打开门缝偷偷向外张望,大人急忙将他拉回屋内,小孩鬼哭狼嚎的声音不时飘荡在空旷的路上。
绿秧半个时辰后,来到了国都皇宫外。官员们早已等候多时,一个个脸红脖子粗。这些人骑在马上与大国师誓死同生共死,连文官也能舞动几下剑招。因此看到大国师,众人毫无疲态,一同跪下行礼:“见过国师,国师一路辛苦。”
先前那个童子出来行礼免礼。在绿秧的带领下,国师一行人如入无人之境,轻松穿过国都皇宫大门,来到早已准备好的清凉殿。武帝也派人协助国师整理内务。
当晚,国师并未召见武帝,武帝也没有提前见国师。迈出第一步,就意味着做出让步,意味着大国师代表国家向对方妥协。这是双方都不愿见到的局面。
国师在清凉殿安顿好后,沐浴更衣焚香,拿出一串磨得锃亮的铜钱,在桌上排成一行,然后拍桌,六枚铜钱纷纷落下,上面是字,下面是光,乾坤定矣,皆为正面,人要在此地寻找,大吉。国师面具下的笑容浮现。既然如此,那就没有必要与武帝对抗。武帝狼子野心自称为帝,法度该斩。可大国师还有几人遵从他的命令。就连云帐国师,也是朝不保夕。
第二天,国师并未接见武帝。只吩咐身边的小童,让武帝将几个孩子找来,想在清凉殿后顺风亭看看武帝的龙子龙女。现在不同以往,武帝也可以拒绝。只是国都崇敬大国师,大国师根本未撤出国都内的护国寺,尚未撕破脸,武帝自然要卖大国师面子。顺风亭中,国师斜倚美人榻,看着武帝的孩子们。太子忆怀带着弟妹拱手道:“忆怀拜见国师。”国师仔细审视这位新选的太子,额头饱满,眉剑眼亮,与当年的武帝相似,犹如一把出鞘的剑,寒光凛然,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傲气。后面的几个弟妹,或灵活或沉稳或天真,各不相同。尤其是昭华公主,从头到脚都透露出与其年龄不符的谨慎。
“大国师被国都取代,不过是早晚的事。”国师心中默默念叨一句。“听说武帝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一个孩子呢?”太子忆怀恭敬地递上一杯茶,国师并未接过,只是静静地看着这位年轻且野心勃勃的太子。
太子显然咳嗽一声,看向弟弟临淮,将临淮被废黜为孝贤王一事轻轻带过。太子话音刚落,国师似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动作停顿了一下,终究还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既无目标,也是浪费时间。“武帝何时有空,何时接见我这个国师呢?”国师耐心地询问了兄妹几个平日饮食后,才开口问此事。
太子忆怀带着弟妹离开,对国师的态度并不确定,于是向武帝禀报此事。武帝听说国师要求,认为狭路相逢,不必让对手久等。批阅完奏章后,故意在御书房停留半个时辰,这才前往顺风亭。此刻,国师正侧身斜头,望着对面从假山中潺潺流下的溪水,汇集成一个小池塘。扑面而来的湿热空气,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武帝朗声笑道:“国师大驾光临,寡人未能远迎,还请国师见谅。”国师听到声音,仍端坐在顺风亭的美人榻上,微微点头。武帝也不多言,直接坐在国师对面。国师身旁两名美貌的白衣侍女见武帝姗姗来迟,心中颇为不满,此时见武帝不分尊卑,竟与国师同坐,早忍不住心中的不满,伸手握住剑柄,拔剑而出。武帝身后侍卫也不甘示弱,拔刀挑战。
国师漫不经心地挥挥手,两名侍女愤怒地收剑入鞘。武帝侍卫也将剑放回身边。国师抚摸着手中的白玉茶杯,淡然问道:“听说西凉已被灭。”声音如同十几年前一样清澈透彻。武帝笑了笑,并未作答,伸手拿起桌上的茶杯,一饮而尽。国师嘴角露出一丝微笑:“灭也好,西凉那些人本来就没什么成就。”说罢,将手中的茶倒入池塘。水面泛起一圈涟漪,随即又恢复平静。过去任何时候,只要国师提出要求,天下无人敢违抗。然而,最近十几年,这片土地上的生灵越来越缺乏尊严,妄图脱离大国师的掌控。眼前的武帝也不例外。
“我今天来,是要向你讨一个人情。”国师终于再次开口说道。“国师有什么事,尽管说。”武帝回答道,见好就收,放下手中茶杯,国师斟了一杯。第二杯茶更加浓烈。国师似乎享受这一点:“我想让忆怀进入我的门下,继承我的衣钵。”武帝从未想过会提出这种要求,有些为难地说:“寡人已经封他为太子,继承你的衣钵恐怕不合适。”国师也明白这事不可能,仍然说道:“你膝下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人人都是人中龙凤,收一个也是两全其美,你还可以立其他三个为太子。”武帝沉声道:“我最喜欢的是临淮,其他孩子我也舍不得让他进国师门下,国师门下固然好,但也不方便守护。”“我还以为你是那种无情无义之人,没想到也像天下父母一样,有一颗爱子之心。倒是看错了你。”国师伸手拍拍武帝肩膀,意味深长地说。国师一番仁慈的话语,武帝也附和道:“即便是高贵的天子,也是血肉之躯,子女长大成人也不容易。”国师收回温和的笑容,语气一转:“你什么时候变得儿女情长了?继承我的衣钵,等我哪天死了,门下一切事务都由他一人管理,大国师易如反掌,岂不比你辛辛苦苦治理西凉容易得多。”武帝每隔几年都会见国师一面,从小到大,国师始终一副面孔。永远白衣黑发,永远青春年少,仿佛与天地同寿。国师去世自然没有其他人容易。武帝对此十分为难:“剩下的几个都担负重任,国师还是不要勉强。”国师见武帝难以处理,似乎妥协了:“另外两个你不肯,你还有一个废太子临淮,不如你将废太子临淮交给我,他反正也没出路,你也看不上他。继承我的衣钵是不可能的,让他在我身边伺候,总比在那穷乡僻壤喝西北风好。”(时间范围:10月1日至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