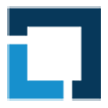梁妈妈慌张辩解:“呃,我也不知,昨日有位贵客指名将她们请了去的,银子都是现付的,我道她们真去侍宴了,真不知她们会到衙门来。”
黄坊使轻轻冷哼了一声,不置可否。
“你可知,她们状告何事?”
黄坊使和梁妈妈都答道:“不知。”
“她们说贵坊丢了一个人,现在人死了,要本官捉拿凶手。”
黄坊使苦笑着对赵谦说,“大人不知,乐坊辛苦,乐坊女子又大多是有些背景的,要不就是被文人权贵捧过了头,都有些娇气,动不动就说辛苦,使性子避去他处,甚至出逃,那都是时常有的事。只是这些女子,即便出走,说还头不过是女子,走也是走不远的,不日便会被寻回。即便有,大人不必忧心。况且近日,下官并未听说乐坊有人出逃,更别说死了。是不是呀,嬷嬷?”
梁妈妈也连忙应和:“是、是的。”
赵谦冷笑一声,道:“那能否劳烦黄坊使走一趟,把贵坊任敏君叫来?”
黄坊使和梁妈妈脸色均是一变。
黄坊使瞪了一眼梁妈妈,梁妈妈连忙跪下道:“大人恕罪,任敏君并不在乐坊。不,不是丢了,而是前些日子那丫头与我生了口角,使小性子了。”梁妈妈指着跪在另一边不敢说话的几名女子,“这几人与任敏君有亲缘关系,就是她们将人给藏起来了。许是我这几日逼她们逼急了,她们这才出来诬告我与坊使。”
赵谦一拍惊堂木,怒道:“大胆刁妇,公堂之上也敢胡扯!你说任敏君没死,那地上躺着的这具尸首又是何人?”
“这……”梁妈妈吓得面色惨白,瘫倒在地,说不出话来。
黄坊使上前一步,道:“赵大人,这尸体损坏如此严重,该是死了多日了,怎么可能是任敏君呢?四日前还有多人在酒宴上见过任敏君。正如嬷嬷所言,任敏君与嬷嬷生了口角,任家姐妹帮她藏了起来,这尸体怕不是这些刁妇随意寻来,搪塞调查的吧?”
任家姐妹纷纷磕头哭喊:“大人明鉴!”
赵谦又一拍惊堂木,喝道:“肃静!”
任家姐妹不敢多言,只能小声哭泣,连头都不敢再抬。
赵谦审视着游刃有余的黄坊使,问道:“有人指认,这尸体就是任敏君的,你又作何解释呢?”
黄坊使看也没看公堂上的人,反唇笑道:“市井泼皮之言,岂有可信之理?”
“黄坊使怎知指认之人是鲁大奎?”钟挽灵插话道,又向堂上拜道:“大人请恕在下无礼,只是黄坊使摆明有意欺瞒大人,在下实在看不下去了,还请大人准在下畅所欲言一吐为快。”
赵谦原本不快有人在公堂之上插嘴,可见说话的是上清宗的人,且维护于他,便松口:“小仙师但说无妨。”
钟挽灵谢过赵谦,道:“首先,还请黄坊使回答,你是如何知道指认尸体的是这鲁大奎?”
“这……”黄坊使脸色微变,稍作思索,道:“我刚堂下旁听了一阵,听到这泼皮说的。”
“说的什么?”钟挽灵追问。
“呃,就是他将尸体寻回的呗。”
钟挽灵笑道:“行。只是黄坊使好像听岔了,寻回尸体时鲁大奎确实在场,可寻回尸体的是我和我师兄。”
“这……”黄坊使转念一想,又道:“那也是鲁大奎带着你俩去找的。也许鲁大奎早就被几个贱婢收买了,尸体也是他找的,故意带你们去找,误导你们。”
鲁大奎见事情绕了一圈又回到自己身上,脸色一变,开口大喊“冤枉”,却被穆晓川一手按住肩膀,顿时哑了声。
钟挽灵稍稍收敛气势,好似被黄坊使说服了一般,点点头。“可以。这点暂且保留。可黄坊使怎么知道这尸首已是死去多日?”
黄坊使讥笑道:“小仙师不食人间烟火。这尸体都已腐坏成白骨,自然是死去多日。”
钟挽灵定定地看着黄坊使,露出一个意义不明的笑容,幽幽地说:“黄坊使要不还是走近些仔细看看?看仔细了,这是腐化见骨,还是创可见骨。”说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黄坊使见尸体上还爬着蛆虫,形容又如此可怖,哪肯靠近。
钟挽灵向赵谦作揖:“还请大人让仵作当堂查验这人究竟是几时死的。”
赵谦点头应允,仵作上前稍作检查便得出了答案。“回禀大人,这人死了不出五日。小仙师说得没错,这是创可见骨,并非腐化而成。”
“那也不一定就是任敏君呀!”黄坊使还想狡辩,指着尸体说,“这尸体面目全无,怎能辨认?无非还是靠这泼皮一面之词。他就是找了一具差不多时间过世的尸体呢?说不定还是亲自行凶制造的尸体呢!”
“你!你血口喷人!”鲁大奎暴起,被穆晓川强行摁住。黄坊使被鲁大奎这一惊吓吓得连退三步。几名衙役连忙扑上来帮着穆晓川将人制服,拖下堂去。
黄坊使心有余悸,转头又见那地上遗体的可怖情状,只得以袖遮眼,一边接着说道:“这尸体情状如此惨烈,岂是人力能为?想必原来应是病死之人,没有妥善安葬曝尸荒野,这才被野兽啃食才成的这般情状。”
赵谦看向仵作。这尸体损伤属实严重,确实不一般。
仵作也不好回答,转而看向钟挽灵。
钟挽灵反唇相讥:“曝尸荒野?这尸体可是我和师兄从半米深的地下挖出的,挖出时尸体外的草席都完整无缺。试问是什么野兽将人啃食至此,还会裹上草席埋在半米以下?衣冠禽兽吗?”说完又道,“这话原本不该由我来说,事已至此我也只能和盘托出了。”言罢,转身面向堂上,道,“启禀大人,黄坊使隐瞒了本案重大信息,他早就知道敏君姑娘遇害之事!”
此言一出,堂内堂外一片哗然,就连跪在地上的梁妈妈和任家姐妹都惊讶地抬起了头。
钟挽灵顿了顿,等场面平静了些,继续说道:“其实在任家姐妹之前,是乐坊先寻的上清宗,委托内容就是寻找失踪的敏君姑娘。”
堂外传来一阵低低的议论声。
“可是当时,黄坊使突然介入撤销了委托。试问,管事嬷嬷不知姑娘下落,只得求助我上清宗,你高高在上的坊使大人如何知晓,且一口咬定敏君姑娘不是出逃。既非出逃,又寻不见人,为何你想着的不是尽快将人寻回,弥补过失,而是掩盖消息,想尽办法撤销委托?”
“这……”黄坊使汗如雨下,“因为……因为我之前就问过最后一日送任敏君回乐坊的轿夫,他说将人安全送回了,那人就在乐坊里藏着。既然在乐坊中就没必要兴师动众了啊!”
“你如何知道那夜是最后一夜?你既然否认敏君姑娘已经遇害,又何来最后一夜?”
钟挽灵走到梁妈妈身边,道:“嬷嬷,你该是知道,公堂之上大人面前,不可胡言。大人明镜高悬,对你们的谎言一目了然。没有戳破,是大人宽仁,想给你们一个机会,你该如实禀告。”
梁妈妈早就被吓懵了,连连点头。
钟挽灵接着问:“那日你请我们在乐坊详谈,可有请黄坊使到?”
梁妈妈摇摇头。“没有,黄坊使是突然到访的,此前我并不知晓。”
“黄坊使经常到访,且对乐坊乐妓了如指掌,亦或者对敏君姑娘特别关心?”
“并没有。”梁妈妈连忙摇头,扭捏答道:“咱们西院多是民间的事宜,坊使大人并不太看重咱们西院,平时也就半月巡察一次。敏君虽然技艺精湛,但圣上和贵妃都不喜琵琶,入宫次数屈指可数,想来也难入坊使大人的眼的。”
钟挽灵点点头,又问:“你可曾告知黄坊使,那夜有轿夫送敏君姑娘回来?”
“不曾!”梁妈妈斩钉截铁道,看向黄坊使的眼中也满是愤怒和不信任,“我从未向坊使提起轿夫之事!”
钟挽灵向赵谦抱拳道:“大人,情况已经很明了了。黄坊使必然与凶手有所勾连,才会对他无从了解之事知之甚详,且对乐坊及我辈追查敏君姑娘百般阻挠,甚至今日还不惜逼着管事嬷嬷在大人您面前接连撒谎。”
堂外人群又是一片哗然。
“你!你居然敢诬告朝廷命官!”
“是不是诬告,抓到凶手一审便知。”钟挽灵义正言辞地反驳道,转身对赵谦拱手说,“大人,既然黄坊使和嬷嬷说有轿夫为证,而那轿夫说辞又与我辈相左,还请大人传轿夫上堂,我辈愿与其当堂对峙。”
赵谦宽慰道:“小仙师多虑了,你们的话,本官岂有不信之理?不过,既然黄坊使和管事嬷嬷都这般说,那轿夫必然有问题。来人!”
两名衙役上前领命。
赵谦问梁妈妈:“那轿夫姓甚名谁?”
梁妈妈面露难色,支支吾吾一阵,磕头告饶:“大人恕罪,我不知他们叫甚……不过!不过,我记得他们在孩儿巷附近住着。带头的叫……叫刘老三!”
赵谦刚想拍案让衙役去拿人,却听堂外一声大吼。
――“不必去了!刘老三来也!”
十一看书天天乐!充100赠500VIP点券!
立即抢充
(活动时间:10月1日到10月7日)